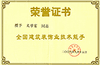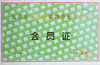2010年,是平常的一年,中国正处于一个快速转型期,经济体制改革正在快速推进,政治体制改革仍处在讨论期。
这一宏大深刻的转型如一切社会转型一样,需要人们承受种种不适应甚至痛苦,它在瓦解人们原有各种价值观、伦理观与社会观的同时,并没有及时整合出新的信仰、价值观与伦理道德等社会底线共识,于是,一种更加强大的系统生成了,它看起来是如此自由又喧嚣,被牢固控制又放纵无羁这两种状态并存,人们乐在其中,也已经分不清楚自己是这个系统的受益者、参与者还是受害者,或者三者都是。
请看有这么多匪夷所思的事:李一道长一人骗得万千追随者;商业领袖唐骏学历造假;方舟子十年如一日打假及遇袭;宜黄拆迁的暴力让一个普通家庭失去生存底线;“我的父亲是李刚”就能逍遥法外……
正如盲人歌手周云蓬所说,我们缺少的不是信仰,而是底线,底线比信仰更重要。
但是,我们不太愿意谈论“底线”,这个词萦绕着一股退居保守、审慎、懦弱、无可奈何、陈腐、龟缩的气息,我们更愿意谈论高屋建瓴、标杆、旗帜、明亮、原则式、坚贞、高洁的东西,它也许可以用一个词代替——“信仰”。
我们谈论信仰,是因为相信中国还有信仰可谈。
许倬云教授对信仰的空洞心存忧虑:“如今的中国,不但政治化,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了商品化,所以就出现信仰真空的问题。”
而与西方或我们的邻国相比,我们的信仰失落就显得格外怵目。哲学家陈嘉映说,变总是要变的,但变的比较缓慢其实更积极更有准备;变的太剧烈,就更有危害,更让人没有把握。中国可能是后一种。
他提到了令人震动的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,他说,当农民工进城脱离了这种生活方式,容易感到茫然若失。这种问题很广泛:当生活形式变化之后,应该如何面对?
一旦问题提出,我们就需要解决方案。远离现代文明、九年如一日风餐露宿在克孜尔石窟临摹壁画的壁画家王征,认为传统艺术能融入现代社会,开花结果,为世人提供精神力量。
然而,就王征提出“文化艺术本身就是救赎”的观点而言,中国有传统,有五千年文明,但需要什么参与其间才能凝聚起传统呢?而在中国文化背景下,宗教与信仰,是一个亟待深究的问题。从孔子开始,“祭神如神在”,那么不祭神呢?神在不在?
可以确定的是,对于信仰的对象不能假设,如果在信仰问题上打折扣,那么一个人的人格精神就不容易庄严,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的精神就不容易庄严。
于是,当“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笑”的宣言大行其道,作为一个极端范例,王征的纯粹与理想化让人深思:这个社会除了物质标杆,是否还有其他东西导航?
幸好我们还有这些沉默者与他们的温暖故事——
无论救助一个得病的孩子,还是地震时的举国救援,社会中的美好、善良的感情和正义的行为还是到处可见。就如同我们不能忘怀舟曲泥石流、上海大火后那焦楼下满街彰显的人性关怀鲜花,它们是这抹灰色中的一点红,它们提醒我们在这个时代还有人在关注终极价值,重视大时代下个体的微小生存。
没有像王征和20万上海市民一样的沉默者彰显的人性关怀,生命会因为失去信仰内涵而无所适从。荒原之所以是荒原,就是因为有力量者从那个时空关系中退场。
所以,我们应该有一些希望,正如许倬云所说,位微言轻的小我背后,是更宽泛的一种大力。上一代和这一代人的信仰,也許已经很难改变,那么对于下一代或者下下一代,他们在信仰上会有突破。“中国人口众多,只要其中的1%开始想问题,讨论问题,那么就有希望。当吃饱穿暖这些基本的问题解决以后,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开始思考问题。”
我们不是仅仅从今年这365天中思考寻找中国人的信仰,毋宁说我们正一边记录着今天的尘世,也一边回头从过去这十年,从改革开放起,甚至1949,乃至1919维新时起,开始寻找的中国人的信仰,那是涉入我们精神的根,那是这棵树的根。
农民工:善良的活着就是我的信仰